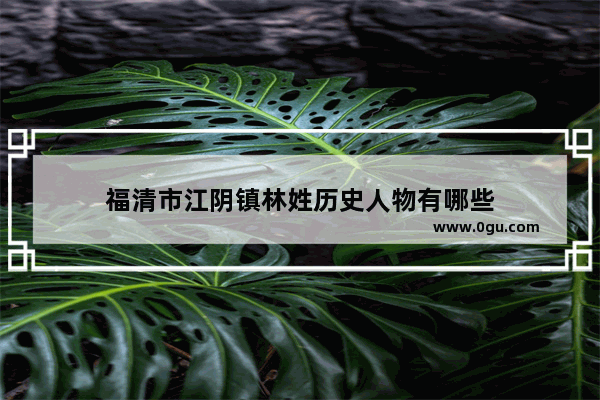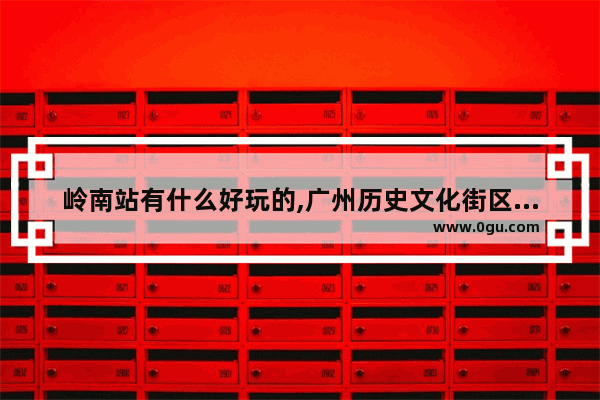您好,零古网为您整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了解福清市江阴镇林姓历史人物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福清市江阴镇林姓历史人物的解答,那么我们一起往下看看。
曹雪芹写通灵宝玉的历史时为什么有“白骨如山忘姓氏”这样恐怖的描写
近日读《红楼梦》,忽为一诗句所惊“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不但惊讶,而且惊悚,惊悚中又带有一丝虚无。
查其所由来,无非宝钗初会通灵宝玉时,作者假托后人写了这么一首诗来嘲弄顽石真相: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其实诗的前四句很好理解。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全书一开始被抛弃的补天石向一僧一道请求得入红尘受享的过程。
只是,作者在这里无论是对“女娲炼石”还是“红尘受享”,都是持一种虚无态度,认为女娲根本没有必要“炼石补天”。换言之,如果女娲没有炼石补天,那么也不会有这块剩余的补天石被抛弃在这里,更不会有后面的补天石因为被抛弃而自怨自艾,“失去了幽灵真境界”,从所谓的“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被携带入红尘,亲近眼前这“臭皮囊”,以更近距离来感受这富贵繁华的衰落过程。
总而言之,都错了,一切都错了,一开始就错了。不但错了,而且荒唐;不但荒唐,而且无稽。是以,这块顽石最开始的落脚地就是“大荒山无稽崖”。

顽石
这不免让人想起林黛玉打趣宝玉参禅的诗“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在这里,作者否定了“炼石补天”这样的建功立业,也否定了红尘富贵、温柔之乡。
人世间汲汲营营所追求的东西,大抵如此,但作者却认为人们因此失去了本真。
当然,“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也让人想起了《庄子·至乐》中的一个例子。大概意思是庄子在途经楚国的时候,在荒郊野外遇到一具骷髅,然后就用马鞭敲着骷髅大发议论,说先生你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是饿死的、冻死的,还是遇到国家灭亡而死的呢?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然后就枕着骷髅睡过去了。
晚上,庄子梦见骷髅给他托梦说,你说的那些都是活人的负累,在我们死人这里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既不用让国君统治,也不用日夜操劳,就算是南面为王的快乐也比不过。
庄子不相信,说那我让司命之神给你恢复身体,让你回到亲友中去,你愿意吗?
骷髅皱了皱眉,忧虑地说:“我才不要放弃南面为王的快乐而去再次经历人世的困苦呢!”
在曹雪芹看来,身而为人,就是“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早知人世要经历如此多的痛苦,一开始还不如不下凡呢!
但是没辙,谁让那个时候的顽石凡心已炽、执迷不悟,非要让一僧一道携带入红尘呢!
正如一僧一道早前告诫的那样: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倒不如不去的好。”
至于第六七句“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无非是说如宝玉、宝钗这样的人,就算真有本事,遇到时运不济,也是枉然。换言之,大厦将倾,覆巢之下无完卵。个人的那种无力感还是很沉重的。当然,这同样也照应了前面一僧一道告诫的话。
通灵宝玉
终于,最为重磅的句子来了,“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白骨如山”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重新回到了“幽灵真境界”,自然也就忘记了自己姓贾还是姓林姓薛,是不是四大家族中人,每个人所承担的家族责任也自然谈不上了。这个时候再来看先前那些事情,无非是男男女女的红尘俗事罢了。古往今来,大抵也都如此。不独宝玉如此,他人亦是如此。凡心已炽的,是所有俗世中人。
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就算我通灵宝玉面对着家族的白骨如山,忘记了自己的姓氏,不过却还能够记得自己曾经身为公子时与红妆们的那一段故事。
贾宝玉和姐姐妹妹们
这也就是作者一开始说的:
“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说白了,就是作者写这部书就是为了纪念那些“红妆”。
然而这样理解的话,却又与前面的将人世价值否定自相矛盾了。毕竟,《好了歌》中也曾说过,“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如若如此,仍是未了。
然而,作者既然写作,说明对人世余情未了,又如何能好。
所谓“好了”,不过是自己绝望之余的一种阿Q式自救心态罢了。
如此说来,佛教,不过是贾宝玉的一个精神避难所罢了。
他的心中有万千柔情,却无处解脱,最后只能跟随一僧一道回到自己最初的地方。
欲知更多《红楼梦》详情,欢迎关注头条号:半瓣花上阅乾坤。
《红楼梦》即使红楼的一场“梦”而已,原名《石头记》“穿金戴玉”亦是如此,按佛家观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色空空,空空色色,人非是缘,缘非是人。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臭幅皮囊,随生命的消失,皮消躯存,所以白骨就是失去灵魂的躯壳而已,同时借助没落的贵族院落及远去贵族生活,给这些骸骨安上不同的灵魂披上不同社会地位及命运,让繁华落尽如云烟,人生就是一场梦境而已,所追逐全是虚无缥缈东西,最终都是尘归尘,土归土……
大清入关后杀了无数汉人,多的时候屠了好几个城池,少的时候也杀不少人。好多历史上都没有记载。说是白骨如山忘姓氏,一点都不夸张!
跛足道人借贾瑞风月宝鉴,重点叮嘱,千万不可照正面,照他的反面!贾瑞死后,代儒夫妇认为此镜是妖镜,遂命架火来烧,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风月宝鉴岂只是让贾瑞看反面,其实是作者让看红楼梦的读者,不要看正面,要看反面。看明亡时,人死骷髅如山,未死之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看反面就能解其中味,明白作者的一把阅辛酸泪!
这样红楼有两面,一面是家族兴衰,伴随情爱、世情冷暖;另一面是明衰灭亡。后一面比较隐蔽,以逃避清朝的文字审查。这样,以第一面为载体,让人痛惜并不忘明亡之历史。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这段描写确实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但这就是曹雪芹写作这部奇书的总基调:“因色而空”。该诗见第八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全诗是这样写的: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之所以在第八回写到,是因为《红楼梦》中最后成就的金玉良缘,也就是衔“玉”而生的宝玉,和配“钗”而生的宝钗结为了夫妻,宝玉、宝钗的见面和相识就在第八回,原文如下:
宝玉亦凑了上去,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
然后就有了“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诗歌,实际上就是为后来这段失败婚姻埋下伏笔,大家知道,宝玉、宝钗成婚的当日,宝玉心爱的黛玉含泪去世,宝玉则痴痴呆呆出家做了和尚。
《红楼梦》中,与这首“白骨如山忘姓氏”意境相同的诗歌还有很多,如第一回中的《好了歌》中有“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好了歌注》中更直接有“昨日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的诗句,表达的都是男欢女爱不过都是一时欢娱的意思,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连《红楼梦》一度的名字就是《情僧录》。
《红楼梦》写自色悟空,不仅有诗文,还有“风月宝鉴”的实物为证。贾府义学塾贾代儒的长孙贾瑞,贪图贾琏之妻王熙凤的美色,结果陷入王熙凤巧设的“相思局”中,病入膏肓之际,医生给他开出的药方中包括这面风月宝镜,这个镜子的正面是王熙凤的裸像,背面是一具骷髅,医生反复交待贾瑞只能看镜子的一面,但贾瑞按捺不住,终于在镜子的照耀下命入黄泉。贾瑞因情而死,因色而空,也是整个《红楼梦》中第一个殒命的人。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装。是批注之语,批者感悟万千。将《红》一书的主要人物进行了说明,“公子”即顽石,即假“宝玉”,“红装“,即金陵十二钗,不外乎卿卿我我,不外乎风花雪月,不外乎昨日陇头埋白骨,今朝红粉卧鸳鸯。可到头来,谁还能记住她们的姓氏,生于何方,歿于何处。这是不爭的事实,一将成名万骨骷,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白骨如山,正是朝代更替的铁证。所以《红》中也隐含皇家爭权夺利的惨烈,及作者对世态炎凉,人生荣辱是一场大梦的认知。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福清市江阴镇林姓历史人物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福清市江阴镇林姓历史人物的1点解答对大家有用。